
基因编辑更快更准更简单
1973年,斯坦利•N•科恩(Stanley N. Cohen)和赫伯特•W•博耶(Herbert W. Boyer)找到了改变生物体基因组的方法,成功将蛙的DNA插入到细菌中。20世纪70年代末,博耶的基因泰克(Genetech)公司对大肠杆菌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带有一个人源基因(这个基因是人工合成的),最后生产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很快,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科学家培育出了第一只转基因小鼠。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就找到了改变生物体基因组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不甚精确,并且难以用于量产。因此,很多基因修饰实验依然既困难又昂贵。
现在,一种名叫CRISPR的新技术,也许将彻底革新基因组编辑。这一技术源自细菌的免疫防御系统,比传统方法更快速、更便宜、更简单。商业化的CRISPR技术公司己经吸引到了大量资金。
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将CRISPR技术应用于艾滋病、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的治疗。然而,因为CRISPR能非常轻易地改变植物、昆虫和人类的基因组,伦理学家担心这会引发一些负面后果。
基因工程领域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改变了现代医学的进程。但是,早期的基因改造方法有两大局限:不甚精确,并且难以量产。那时,DNA插入基因组的行为是随机的,科学家只能祈求好运,但愿自己能得到一个有用的突变。1990年,研究人员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他们设计出能在特定位点对DNA进行剪切的蛋白,突破了第一个局限。但是,每想要修改一段DNA序列,他们都必须设计一个新的蛋白,这种工作非常耗时,并且十分艰苦。
时间终于到了2012年。瑞典于默奥大学(Ume? University)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领导的研究人员报道,他们在细胞中发现了一种遗传机制,能让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编辑基因组,并且过程十分简单。此后不久,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课题组运用这种技术,一次性地对细胞基因组的多个位点进行了修改。
这种先进的技术已经加快了基因工程产业的发展,对遗传学和医学也有深远的推动作用。科学家现在只要几周时间,就能按需定制出经过基因改造的实验动物,省去了从前一年的工作量与时间。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该技术,探索艾滋病、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治疗方法。该技术将生物体的基因修饰过程变得相当简单与廉价,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甚至开始担心,这会催生负面效应。
这种技术名叫CRISPR,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即成簇、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的缩写。利用这种序列,细菌可以对侵袭过它的病毒产生“记忆”。自从日本科学家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CRISPR之后,科学家就一直在研究这种奇怪的基因序列。然而,直到杜德娜和卡彭蒂耶偶然注意到一种名叫Cas9的蛋白,CRISPR才显示出它作为基因组编辑工具的巨大潜力。
2011年,杜德娜和卡彭蒂耶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一次科学会议上相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团队都在研究细菌防御病毒入侵的机制;他们都已经确认,细菌可以记住以前入侵过自己的病毒的DNA,以此来识别病毒,当该病毒再次入侵时,它们就会立刻认出“敌人”。
那次会议后不久,卡彭蒂耶和杜德娜决定合作。当时,卡彭蒂耶在于默奥大学的实验室刚刚发现,链球菌似乎会用Cas9蛋白来“捣碎”突破其细胞壁的病毒。于是,杜德娜在伯克利的实验室,也开始探究Cas9蛋白的作用机理。
很多科学发现的背后都有一连串巧事,CRISPR的故事也不例外。卡彭蒂耶实验室的克日什托夫•黑林斯基(Krzysztof Chylinski)和杜德娜实验室的马丁•伊内克(Martin Jinek)在毗邻的城镇长大,说着同样的波兰方言。杜德娜说:“他们开始通过Skype聊天。两人一拍即合,然后就开始分享数据、讨论做实验的想法。这个项目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两个实验室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或许可以用Cas9蛋白来进行基因组编辑。基因组编辑是基因工程中的一种方法,酶是这一过程中的“分子剪刀”,可以剪切DNA。这种酶名叫核酸酶(nuclease),能在特定的位点切断双链DNA。DNA断裂后,细胞会对断裂位点进行修复。有时,细胞中一些人为导入的基因片段,会在修复的过程中插入这些位点。杜德娜和卡彭蒂耶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科学家如果想改变或关闭一个基因,最先进的方法,是定制一种能找到特定DNA位点并对其进行切割的酶。换句话说,每修饰一次基因,科学家都不得不设计一种新的蛋白,专门针对想要修饰的DNA序列。
但杜德娜和卡彭蒂耶意识到,Cas9蛋白——这种链球菌用于免疫防卫的酶,会用RNA来引导自己找到目标DNA。为了探测作用位点,Cas9-RNA复合物会在DNA上不停“弹跳”,直到找到正确的位点。这一过程看似随机,其实不然。Cas9蛋白的每次弹跳,都是在搜索同一段短小的“信号”序列。Cas9会附着到DNA上,检测邻近的序列是否和充当向导的RNA匹配。这种RNA叫做向导RNA(guide RNA,简称gRNA),而只有当gRNA和DNA匹配时,Cas9蛋白才会对DNA进行切割。如果能将这套天然的RNA向导系统利用起来,研究人员在切割DNA位点时,就不用每次都构建一种新的酶了。基因组编辑可能会因此变得更简单、更便宜,也更有效。
这个横跨大西洋的团队一起对Cas9蛋白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杜德娜还能清楚地记起那个时刻。他们的实验室坐落在伯克利校园边缘一个绿树成荫的山坡上,对面就是希腊剧院,彼时还在做博士后研究的伊内克一直那里在对Cas9蛋白进行实验。一天,他来杜德娜的办公室讨论实验结果。面对伊内克和黑林斯基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他们陷入了沉思:在自然界中——也就是在链球菌体内,Cas9蛋白倚靠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RNA,来引导自己寻找DNA上的正确位点。
如果在保留其向导功能的前提下,将两条gRNA整合成一条RNA链,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只需修饰一个RNA序列,研究人员的工作速度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gRNA序列与目标DNA序列之间存在精妙的互补关系,利用这种关系构建一条gRNA,比定制一个核酸酶更容易。
“看着这些数据,我们突然就开窍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杜德娜说道,“我们意识到,其实可以将这些RNA分子设计成一条gRNA。一套由一个蛋白质和一条gRNA组成的系统,就足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基因修饰工具。我打了个寒颤,心想,‘天哪,我要赶快跑到实验室去,如果这能成功的话……’”
他们真的成功了。结果超出了杜德娜的设想(尽管她本来就抱有很高的期待)。2012年8月17日,当杜德娜和卡彭蒂耶将他们对CRISPR-Cas9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众时,该领域的科学家立刻认识到这一技术的变革性力量,他们都想知道CRISPR-Cas9究竟能做什么,一场全球性竞赛由此拉开序幕。
CRISPR是怎样工作的?CRISPR 是细菌的“武器”,它能“捣碎”入侵细菌的病毒的DNA。科学家可以利用这套工具,改变他们想要修饰的DNA序列。和从前的基因组编辑方法不同,CRISPR 系统采用一个通用酶——Cas9 来执行剪切。研究人员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制造一个gRNA来引导Cas9,而合成一条RNA,远比合成一个酶更加容易。
2013年之前,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将CRISPR-Cas9应用于植物和动物细胞——它们比细菌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看来,这和复活尼安德特人与猛犸象一样激动人心。在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领导的团队用CRISPR技术来改变人类基因,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CRISPR-Cas9很快成为了投资的热点。一年多以前,杜德娜联手丘奇、麻省理工学院的张峰和其他研究人员,共同成立了爱迪塔斯医药公司(Editas Medicine),他们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以开发一类新的、基于CRISPR的药物(该公司还没有透露他们首先瞄准的是哪类疾病)。2014年4月,获得2500万美元投资的CRISPR医疗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在瑞士巴塞尔和英国伦敦成立,他们的目标也是开发基于CRISPR的疾病疗法。爱迪塔斯医药公司和CRISPR医疗公司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开发出相应的疗法,然而,实验室的供货商们已经在向世界各地的客户销售可以立即用于动物注射的CRISPR材料,并开始为客户定制经CRISPR改造的小鼠、大鼠和兔子。
今年,我在一个潮湿的夏日拜访了位于圣路易斯的SAGE实验室(SAGE Labs),它是第一批获准使用杜德娜的CRISPR技术来改造啮齿类动物的公司之一。在那里,我能亲眼见识CRISPR是如何起作用的。SAGE实验室向大约20家顶级制药公司,以及众多高校、研究所和基金会供应实验材料。英国剑桥的生物技术公司地平线发现集团(Horizon Discovery Group)早前也已独立涉足CRISPR产品的研发;2014年9月,他们又以4800万美元收购了SAGE实验室。SAGE实验室位于一个工业园区内,建在一条马路尽头的一组低矮的办公建筑里。这里的科学家收到一个来自实验室的网上订单: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实验室为研究帕金森病,订购20只敲除了Pink1基因的小鼠。建筑新修的侧楼耗资200万美金,里面是为客户定制的基因改造大鼠,以及其他经CRISPR改造的啮齿类动物。这些动物生活在超净、恒温的笼子里,笼子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从地板一直排到天花板。工作人员填写订单、选出相应的20只大鼠,将它们轻轻地放在盒子里打包,然后空运到加利福尼亚——整个流程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精神分裂症或疼痛控制,也可以这样订购实验动物。
不过,如果仓库里没有客户想要定制的那种动物,流程就不一样了。例如,有一个客户想要研究帕金森病和一种新发现的可疑基因(或者一个基因的特定突变)之间的关系,当他到SAGE实验室订购啮齿类动物的时候,有几个选择。SAGE实验室的科学家能用CRISPR技术“关掉”目标基因,制造一个突变;他们也可以关掉目标基因,然后再往里插入一个人源基因。从帕金森病到囊性纤维化,再到艾滋病,许多疾病都和基因突变有关。过去,科学家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培育出这些带有复杂基因突变的实验动物。但CRISPR不同于以往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利用这种技术,研究人员能同时在细胞内快速地改变多个基因。培育基因工程动物的时间已因此缩短到几周。
SAGE的员工首先使用化学试剂盒,合成客户定制的DNA,以及与这条DNA相匹配的RNA。他们将RNA和Cas9蛋白在培养皿里混合,一套具有基因组编辑功能的CRISPR工具就诞生了。然后他们会花上大约一周的时间,用一种外形类似于扫描仪的仪器,测试该工具在动物细胞内的功能。这种仪器能够发射电流,将CRISPR工具注入细胞。进入细胞的CRISPR工具会立刻开始工作,对DNA进行剪切,进行小量的基因插入与删除。CRISPR并非100%有效:在某些细胞里,它们会剪切DNA、制造突变,在另一些细胞里则完全不起作用。为了观察CRISPR的表现究竟如何,科学家会从细胞中收集DNA,将它们集中起来,并将目标位点附近的DNA片段复制多个拷贝。他们会对这些DNA进行处理与分析,然后查看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分析结果。如果CRISPR成功切开目标位点,制造出突变,屏幕上就会显示出一条模糊的条带,并且,CRISPR剪切过的DNA越多,条带就越明亮。接下来,“战场”转移到了侧楼的动物实验室里。科学家就是在这里制造出经基因改造的胚胎,以及突变过的啮齿动物。生物学家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戴着外科手套、身穿蓝色的长袍、戴着套鞋和蓬松的帽子,弯腰伏在解剖显微镜前。他用玻璃移液管的尖端吸起一个大鼠胚胎,然后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将胚胎转移至另一台装有机械手臂的显微镜上。他将胚胎放到载玻片上的一滴液体里,固定到台面上。现在,CRISPR就要发挥它的魔力了:他用右手控制操纵杆,一只机械手臂将一根空的玻璃针头扎入胚胎。
从显微镜的目镜看去,胚胎中来自双亲的两个原核(pronucleus)就像是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布朗轻轻推动细胞,直到其中一个原核移到针尖的旁边。他点击电脑鼠标,一滴含有CRISPR的液体从针头喷出,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原核立即像一朵快速盛开的花一样膨胀开来。布朗运气不错,一个突变细胞就此诞生了。SAGE实验室中有3个技术员,他们一周4天、一天300次地重复着这项工作。
布朗将完成注射的大鼠胚胎吸入移液管,移进培养皿,存储在加热至动物体温的培养箱中。最后,他需要将30~40枚经过修饰的胚胎注射到******母鼠体内。20天后,******大鼠将怀上5~20个“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到10天大的时候,SAGE实验室的科学家将抽取组织样本,检测哪个“孩子”带有改造过的基因。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候,”布朗说道。20个胚胎中,可能只有1个能被成功改造,而改造成功的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源动物(founder animal)。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会庆祝一下。在我们看来,SAGE实验室的科学家制造RNA、注射胚胎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很多实验室也在用同样的步骤培养基因工程动物。正如SAGE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斯莫勒(David Smoller)说的那样,这是可以“量产”的基因组编辑技术。
CRISPR已经勇猛地踏上了商业化的征途,研究人员和商人都在为这种技术设想新的商业用途,其中的某些想法甚至有些狂妄。运用这种技术,医生或许可以在怀孕早期的妇女体内,改造与唐氏综合征有关的异常染色体;育种人员可以重新向抗性杂草的基因组中引入对除草剂敏感的基因;我们还可以复活已经灭绝的物种。这当然会让有些人感到害怕。比如,最近就有一些警告性的头条报道,将这种技术形容为“扮演上帝的好方法”,或者“瓶中妖”。这些文章担心,当我们急于摆脱疟蚊,太想治好亨廷顿病,或者期望“设计”出更好的婴儿时,我们也可能是在创造一个充满有害新基因的“侏罗纪公园”。
以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的“灭蚊项目”为例。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生物安全分析师托德•库伊肯(Todd Kuiken)认为,战胜疟原虫是一回事,但要消灭这种寄生虫的载体,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项任务。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根除疟疾这种每年感染两亿人、杀死60万人的疾病,我们就不得不小心,自己是否会制造出10个新麻烦。“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真要这样做吗?’如果答案是‘是’,我们有哪些可用的系统?有什么样的保障措施?”
科学家正在快速行动,他们希望预见CRISPR技术最可能的危害,并制定应对措施。2014年7月17日,当哈佛大学的团队发表一篇讨论如何用CRISPR消灭疟蚊的论文时,他们也在呼吁公众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也指出了基因改造在技术与监管上的窘境。该团队的生物伦理学家让蒂宁•伦斯霍夫(JeantineLunshof)说:“CRISPR的发展如此迅猛,很多人还没听说过这种技术,但是我们确实正在使用它。这是一种新现象。”现在,在伯克利的创新基因组计划(Innovative Genomics Initiative)的框架下,杜德娜正在组建一个团队,专门讨论应用CRISPR的伦理问题。如果对伦理问题的担忧,扑灭了人们对CRISPR的热情,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例如,2014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报道,他们直接从尾部向动物体内注射CRISPR,治愈了患酪氨酸血症(tyrosinemia,一种的罕见肝脏疾病)的成年小鼠。这种疾病由一种突变的酶引起。研究人员向小鼠体内注射了3种gRNA序列和Cas9蛋白,以及突变基因的正确DNA序列。小鼠的每250个肝脏细胞中,就有1个插入了正确的基因。接下来一个月,被“修正”的肝脏细胞蓬勃生长,最终取代了1/3的病变细胞——这足以使小鼠摆脱上述疾病。2014年8月,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病毒学家卡迈勒•哈利利(Kamel Khalili)领导的研究人员报道,他们已经用CRISPR在数个人类细胞系中对HIV病毒进行了剪切。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哈利利一直奋战在对抗HIV/AIDS的前线。对他来说,CRISPR是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尽管艾滋病治疗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今天的药物仅仅能控制病毒,仍然不能根除疾病。不过,运用CRISPR,哈利利团队已经彻底从细胞中清除了HIV的完整DNA拷贝,将受感染的细胞转化了成无病毒细胞。并且,除了“清洗”已经感染病毒的细胞,CRISPR还可以将一段病毒序列整合进未受感染的细胞中,对其进行免疫——正如杜德娜和她的团队在原始的细菌中观察到的那样。你可以将这种手段称作“基因疫苗”。哈利利说:“这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如果你在两年前问我,‘你能精准地切割人类细胞中的HIV吗?’我可能会说这非常困难。但现在,我们做到了。”
可编程的细胞

通过轻轻地挤压细胞,就可以让一些大分子或纳米材料进入细胞,进而改变细胞的运作。
假如人类能让体内的细胞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运作,比如让它们适时地合成胰岛素,或去攻击肿瘤,那么许多健康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不过,实现这一愿望并非易事。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利用病毒穿透细胞膜,对细胞进行干预,但这样会对细胞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不经意间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他们当时正尝试用显微水枪向细胞注入一些大分子和纳米材料。这些物质可以改变细胞的运作机制,同时又能保证细胞存活。化学工程师阿蒙•沙雷(Armon Sharei)发现,水枪的冲击使部分细胞的外形产生了短暂的畸变。
令人吃惊的是,当细胞的外形处于畸变状态时,注射的物质成功地进入到了细胞内。沙雷说道:“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让细胞在足够短的时间内产生形变,便可暂时克服细胞膜的阻碍。”不管怎样,显微水枪还只是一种较为粗放的方法,下一步工作是找到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挤压细胞。
为此,在显微流控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克拉夫•F•延森(Klavs F. Jensen),以及另一位生物领域的先锋人物罗伯特•S•兰格(Robert S. Langer)的带领下,沙雷开发出了一种以硅和玻璃为材质的微芯片。这种芯片的表面,预先蚀刻了供细胞流动的通道,随着细胞流动的方向,通道逐渐收窄,直到细胞无法继续向前行进。此时,被卡住的细胞因受挤压而产生形变,细胞膜上便会出现小孔。这些小孔的直径,足够许多可改变细胞运作的介质通过,如蛋白质、核酸、碳纳米管等。
这项技术甚至能将介质成功引入脆弱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中,这些细胞无法经受以前那种挤压方式的摧残。“这项技术适用的细胞种类之多,让我们都始料不及,”沙雷介绍道。
自这项技术问世以来,沙雷所在的研究团队已经开发出了16种适用于不同细胞的芯片。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芯片陆续问世。而且,在现有每秒挤压50万个细胞的基础上,相关设备的处理效率还将更上一层楼。该团队已经成立了一家名为“SQZ生物科技”的公司,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法国、德国、荷兰及英国的科研人员有望很快用上该技术。
透明动物

通过注入特殊化合物,可以使动物变得通体透明,这项技术将成为生物医学领域发展的助推器。
5年前,维维安娜•格勒迪纳鲁(VivianaGradinaru)还在神经生物学实验室里,缓慢地处理着小鼠大脑切片的二维图像,并将其合成为三维模型。一天,她慕名参观了“人体世界”标本展。整个展览最让她着迷的,是经过塑化处理、完整的人体循环系统。这件展品让她深深感到,类似的处理方法可以运用到她的研究领域中,大大地提高实验效率。
“组织剥离”概念的提出已有100多年,但当时的方法,如使用溶剂浸泡等,效率十分低下,通常也会破坏标记细胞所需的荧光蛋白。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格勒迪纳鲁,与已故神经免疫学家保罗•帕特森(PaulPatterson)实验室的同事一起,开展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替换组织中的脂肪分子——正是脂肪使得组织不透明。不过,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可替代脂肪的物质,用以支撑组织的结构。
最终,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方法:首先对啮齿类动物实施安乐死,并将甲醛注入其体内,利用心脏将甲醛泵至动物全身;之后,剥去动物的皮肤,从血管注入一种名为丙烯酰胺单体(acrylamide monomers)的白色无味化合物。丙烯酰胺单体可在动物体内建立一个具有支撑作用的水凝胶网,取代动物组织内的脂肪,并使其呈现无色状态;两周之内,这种物质可以使一只小鼠变得通体透明。
这种方法诞生后不久,他们便开始尝试着绘制透明小鼠的完整神经网络。透明器官让他们梦想的不少研究都成为现实,比如分辨周围神经——这类人们从前知之甚少的细微神经束。再比如向透明小鼠尾部注入带有荧光标记的病毒,观察病毒如何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小鼠的大脑。“掌握这项技术,就好比拥有了洞察世间万物的‘透视眼’,”格勒迪纳鲁介绍道。透明器官一方面可降低实验中人为误差的概率,另一方面可提高实验效率,丰富实验数据,同时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格勒迪纳鲁愿意向任何有需要的实验室提供她的水凝胶制作方法。下一步她将把这一技术推广到癌症以及干细胞领域的研究上。
简易快速的纳米显微镜
一种可以拍摄纳米粒子的电子显微镜能快速检测药物、爆炸物中的分子信息。
具备纳米尺度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价格动辄高达数百万美元,准备样品也非常麻烦。对于专业的研究型实验室来说,这样的状况还能够接受,但如果要快速扫描产品样品,来查看内置的微尺度水印呢?
纽约大学物理学家戴维•格里尔(David Grier)和同事研制出的一种新型全息显微镜,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以商用蔡司(Zeiss)显微镜为基础,将它的白炽灯光源换成激光光源。激光照射到待观察的样品上,然后发生散射,形成由激光束和散射光互相干涉而成的三维图像(即全息图),并由摄像机录下。
数十年以来,科学家已经可以生成微尺度物体的全息图像,但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总是很困难。这就是格里尔这项发明的价值所在。他的研究小组编写了一种软件,能够快速求解描述光在球体上散射的方程中的未知参数。这些参数中包含了关于散射物体的所有信息。由于这种显微镜具有纳米级的分辨率,研究人员得以追踪胶体中悬浮的粒子(例如涂料样品中漂浮的纳米珠)。同时,它的成本只有电子显微镜的十分之一。
格里尔希望这种仪器能够提供一种快速而经济的方式,用来观察产品内部的单个粒子。设想一下,涂料桶或洗发水瓶中每滴液体都含有标注了产品生产信息的微粒——就像指纹一样。格里尔还补充道,这种显微镜同样容易“读”出“加盖”在药物、爆炸物及其他物品中的分子信息。
液体发电
唾液也许会成为医用设备的新能源。
默罕默德•穆斯塔法•侯赛因(Muhammad Mustafa Hussain),这位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教授,毕生致力于极微型装置的研发。他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研究:“小东西拉近了我们与未来的距离。”于是,当他在2010年着手研究高效、可再生的发电设备,为偏远地区的净水或医疗诊断提供充足的能源时,他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小巧。不过,利用唾液驱动燃料电池,却是他在研究开始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这个“吐口唾沫”的点子来自于当时侯赛因实验室的同事、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贾丝廷•E•明克(Justine E.Mink,现为陶氏化学公司的研究员)。那时,明克正尝试开发一种可以植入人体,安放在胰腺附近监测糖尿病人血糖水平的微型装置。微生物燃料电池——这种通过向细菌提供有机物(唾液中也富含有机物),利用细菌代谢产生电流的方法映入了她的眼帘。碰巧她和侯赛因的项目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因此两人找来高导电性的石墨烯电极,在上面附着了唾液细菌,在一周之内,这些细菌产生了1微瓦(百万分之一瓦)的电量。
虽然1微瓦看起来微不足道,却足以驱动诸如芯片、诊断工具、或是明克的糖尿病监测仪这样的微型设备了。侯赛因现在正与3D打印人造器官的公司合作,将他的燃料电池嵌入人造肾脏中,并通过各种体液为电池充电。他说这只是他宏伟目标的第一步,今后,他打算帮助贫困国家,利用工业废弃物中的有机物来发电,并将电力用于海水淡化。
“原子积木”搭建新奇材料

新材料的发现总是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推动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最后来到硅时代的动力。
乐高积木是一种很有魔力的塑料玩具,它不断地激发出一个又一个新创意。乐高积木的塑料组件体积很小,能按照不同方式组合到一起,从而变成神奇的汽车、设计巧妙的城堡和许多其他结构。而今天,新一代材料科学家正受乐高积木的启发,将这种组合方式应用到纳米世界。
这里的积木组件是一些层状材料。这些材料最薄可以达到仅有一层原子,可以按照设计好的结构,以精确的顺序一层一层地叠加到一起。这种前所未有的精密组合方式,能够制造出全新的物质,这些物质具备前所未有的电学和光学性能。科学家们进一步设想,可以利用这些物质,制造出几乎没有电阻的导电材料,运算能力更强大、运行更快的计算机,以及可弯曲、可折叠而且非常轻的可穿戴电子器件。
这些突破性的研究,是因石墨烯(graphene)的出现才产生的。石墨烯是一种片状结构的石墨新材料,厚度只有一个原子,其原子结构是一个个重复的六边形,看起来就像铁丝网围栏一样。2004年,我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同事从块状石墨上分离出了单层石墨片——石墨烯,使用的方法是利用胶带从块状石墨顶层剥离出一片片1个原子厚的晶体。过去10年间,研究人员发现了几十种可以用这个方法剥离的块状晶体,而且这样的晶体越来越多。云母(Mica)就是其中的一种晶体,还有一些具有独特名字的材料,如六方氮化硼(hexagonal boron nitride)和二硫化钼(molybdenumdisulfide)。
这些晶体层被认为是二维材料,因为对任何材料来说,其最小厚度就是单个原子厚度(稍厚点的晶体,如3个左右的原子厚度,也可以看做是二维的)。而根据制造者的需求,晶体层的其他尺寸——宽度和长度,可以非常大。由于二维晶体具有许多非常独特的性能,在过去几年里,它们已经成为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领域非常热门的话题。
我们可以将这些晶体层非常稳定地叠放在一起。它们并不是按常规方式通过化学键相连的,比如共享电子的共价键。当它们相互靠得非常近时,原子间会通过大家熟知的微弱的范德华力相互吸引。这个力通常不够大,无法将多个原子或分子聚合在一起,但因为这些二维晶体层的原子非常密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非常近,因此这些力累加到一起,会变得很强大。
为了理解这种材料究竟会带来什么诱人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一下室温超导。要实现无能量损失的电流传输,而且又不需要将设备置于超低温环境中,这一直是几代科学家的梦想。如果发现了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材料,对人类文明一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原则上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实现。到今天,超导材料的最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从正常态转变为超导态时的温度)也要在-100℃以下。过去20年来,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
我们最近发现,用我前面描述的方法,可以将许多氧化物(由至少一个氧原子和许多其他元素组成的化合物)超导体分解成厚度为1个原子的片层结构。如果我们换一种顺序,将各层重新组合,并且在中间添加一层其他晶体层,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氧化物的超导性依赖于层间距离;我们还知道在晶面之间增加一层额外的晶体层,可以将弱导电甚至绝缘材料变为超导体。测试这一想法的真实实验还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制备原子尺度的“乐高材料”的相关技术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而且将复杂的多层结构组合到一起也很困难。
目前,这些结构所含的不同晶体层很少能多于5种,一般只含两种或3种不同的晶体层,一般是由石墨烯片与二维材料(绝缘体氮化硼、半导体二硫化钼、二硒化钨等)组成。因为这种堆叠结构含有多种材料,经常被看作异质结构。它们现在的尺寸都非常小,通常长宽都只有10微米,比头发的横截面还小。利用这些堆叠结构,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探索其新奇的电学和光学性能以及新用途。这些结构还有一个有趣的特性:它们不仅非常薄,还非常柔软,而且透明。这就为制备多种形状的发光设备提供了可能:研究人员有机会制备出可折叠的显示屏,当使用者需要大一点的显示屏时,就可以将显示屏展开;也可能制备出新的计算机芯片,耗能要比现在的芯片低很多。
研究人员在研究这类新材料时,如果能有一些重大突破,我们相信,一定会发展出相应的大规模制备技术,以实现其工业应用。就像石墨烯和其他一些二维晶体材料那样。最初制备那些材料时,仅能得到几微米大的微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几百平方米大的片状材料。
目前,还没有人发现这类新材料有什么改变世界的“杀手级应用”,然而,这一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让很多科学家感到兴奋。新材料的发现总是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推动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最后来到硅时代的背后力量。纳米尺度的“乐高积木”代表了人类从未制造过的新材料。现在,我们只能猜想未来的一切,但我们相信,这种新材料带来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
声波充电

201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还是古生物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的梅瑞狄斯•佩里(Meredith Perry)伸手去拿她的笔记本电脑充电器。
突然间,一个想法跃入了她的脑海:是否有一天能抛开这些麻烦的充电线呢?她随即开始寻找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途径。
佩里了解到,已经有基于磁共振和电磁感应的无线电力传输技术了,但它们的传输距离有限。限制它们的是平方反比定律(inverse square law),即电磁辐射的强度与辐射源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然而,机械振动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用压电转换器从空气中获取振动能量,就可以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因为声音其实就是振动的空气粒子,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应该能够传输能量。而安全、安静且高能的超声波是个完美的选择。
当佩里同本校教授以及其他专家讨论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想法不可行,因为无法利用超声波提取出足够的能量来为电子设备充电;而且,如果她真要尝试的话,还会遇到大量的电子工程和声学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知道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佩里说,“而且没有人能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绝对无法实现。”所以,她找到了uBeam公司,来研发这项技术。
目前,他们已经开发出了uBeam发射机的原型样机。它相当于一台定向扬声器,可以将超声波聚焦,产生一个能量“焦点”;与电子设备相连的接收器负责接收这股能量,并将其转化为电能。她计划在两年内推出第一批产品。
佩里说,通用无线充电系统不仅能让我们不用再携带目前各式各样且互不兼容的电线和充电器,还可以保证移动设备在进行高耗电操作时不会用尽电量。摆脱电线的束缚,还能带来崭新的室内装修设计思路。此外,目前载有沉重输电线缆的飞机、汽车、太空船等运载工具,重量也可以大幅降低。
“总的来说,无线充电技术将彻底改变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作用方式,”佩里说,“我们将不再受制于电源插座。”
储存热能的电池
基于热耦合效应的新型电池,可以将白白流失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一技术拥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在工业生产中,每年都有100亿瓦特的电量以热能的形式被浪费掉了,而这些能量足够为1000万户家庭提供照明用电。通过热电效应(thermoelectric effect),就可以利用温差发电,把这类热能转化为电能。但是,这样也只能利用其中的一部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杨远(Yuan Yang)解释道:这是因为几十年来的研究都表明,需要达到500℃以上的温差,才能产生出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能量。不幸的是,据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估计,在美国每年浪费的能量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以低于100℃的温度逃逸掉的。
杨远和他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陈刚(Gang Chen),以及博士后研究员崔屹(Yi Cui)和李硕祐(Seok Woo Lee)一道,研发出了一种温差仅为理论值1/10(低至50℃)的发电技术。这种技术的关键是利用了热耦效应(thermogalvanic effect,与热电效应有类似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材料整体的温度都随电压而变化,而非仅在电池中产生温度差。研究团队使用不带电的电池芯,配以铜电极,在高温时进行充电,然后再让它们冷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池的放电电压比为它们充电时所用的电压更高。换句话说,用于加热电池的能量被电池以电能的形式收集了起来。
直到近两年,电池电极的效率才达到能将如此小的温差转化为电能的程度,杨远介绍说。而且在实现商业化前,这项技术还需要很多的研究工作来进一步完善。但是,人们迟早会建起由大量电池组筑起的“围墙”,环绕在工厂烟囱或发电厂的周围,将以往白白浪费掉的热能转化为电力。“这一场景非常诱人,”杨远说,“因为被浪费掉的热能随处可见。”
新型聚合物“泰坦”
环保、高强度、可自我愈合、可回收的聚合物,将改变汽车、飞机等诸多行业。
当化学家珍妮特•加西亚(Jeannette García)在最近用过的一个烧瓶里,发现了一块糖果大小的白色材料时,她压根不知道到自己做出了什么东西。这种材料紧紧附着在玻璃上,所以只能用锤子打碎烧瓶才将其取出。但是,当她再次用举起锤子,去敲打这块材料本身时,后者却毫发无损。“当意识到它的有多坚固时,我就知道必须要弄清楚我究竟做出了什么东西,”加西亚说。
加西亚是IBM公司阿尔马登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最终,她在几位同事的帮助之下解开了这个谜团。他们发现,这种令人吃惊的材料是一类新型热固性聚合物。这是一类极为坚固的塑料,能用于从智能手机到飞机机翼等众多产品中。虽然在全球每年生产的聚合物中,热固性材料就占到了三分之一,但是它们很难被回收利用。而加西亚发现的新材料(被称为“泰坦”),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种可回收的、具有工业级强度的热固性材料。
传统热固塑料无法回收重塑,而上述新型聚合物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进行重新加工。在2014年5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加西亚和同事介绍了他们的发现。
预计,全球对耐用且可回收的塑料产品的需求将很快大幅攀升。到2015年,欧洲和日本都将要求厂家在生产汽车部件时,可回收材料的比例要达到95%。“‘泰坦’恰恰可以完美地满足这种需求,”加西亚说。此外,她相信这种新材料最终还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应用中,包括抗蚀抗菌涂层、给药设备、粘结剂、3D打印、水净化领域等。
“泰坦”还有其他优点。加西亚和同事发现,这种材料还有第二种形态——在低温时,它会呈现出可自愈合、类似凝胶的形态。这种形态被研究人员称为“海德鲁”(Hydro,意为水)。“如果将海德鲁切成两半,再放回一起,它们会立刻互相粘结,”加西亚介绍说。这样,“泰坦”就可以用作粘合剂,或者自修复涂料,其他相关的化学产品也将陆续被开发出来。“(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型聚合物,而且还是一种新的聚合物生成反应。”加西亚说。
视力矫正显示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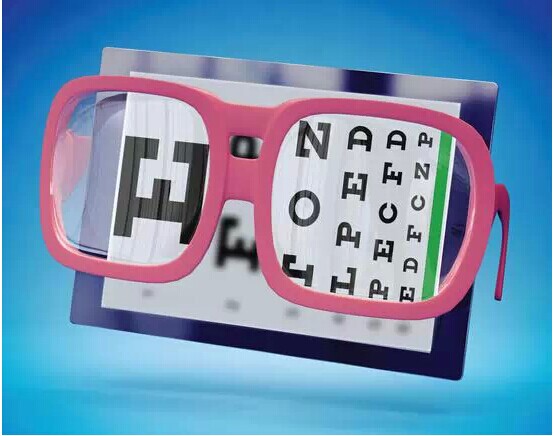
在美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40%的人在阅读时都需要戴眼镜;而对于80岁以上的人群,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近70%。“随着年龄的增长,屈光不正(refractive error)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学助理教授戈登•维茨斯坦(Gordon Wetzstein)说。
但是,无论框架眼镜还是隐形眼镜,都有不甚理想的地方。举例来说,一个远视的人,在开车时观察交通路况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查看速度表或GPS导航的时候就需要戴眼镜了。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视力矫正显示屏,即能根据用户的情况给显示屏“戴上眼镜”,维茨斯坦说。
与麻省理工学院(维茨斯坦曾在这里工作)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合作,维茨斯坦研制出了这种显示屏。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标准高分辨率显示屏的基础上,他主要做了两项改动:一是打印一种低成本的、布满小孔的透明薄膜,覆盖在屏幕上;二是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编写算法,来判断用户相对于显示屏的位置,并根据他(她)的验光处方来调整投射的图像。当调整过的图像通过显示屏透明薄膜上的小孔阵列时,在软硬件的共同作用下,屏幕上会产生误差,正好同视力误差相抵消,在用户眼中形成清晰的画面。这种显示屏能为近视、远视、散光和其他更为复杂的视力问题提供相应的矫正。2014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 for Computer Graphics)年会上,研究人员首次展示了这项技术。
据维茨斯坦介绍,在少量用户中进行的非正式测试显示,该技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不过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进一步完善。研究人员还计划开发一种滑动条,用于手动调整显示屏的焦距。维茨斯坦说,对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来说,这项技术尤为便利,因为在某些地区,获得移动设备要比通过医生处方购买眼镜更容易。
更多新闻请点击:http://www.yanke360.com/news/


